
正是有了七星渠上的积累,有了王非凡一字千金的“播”字,从渠上回来,我到了大队部,暂时告别了抢毛驴送粪、背背斗强苦力农活。大队书记说是先让我到大队当当电工,熟悉熟悉全大队的情况,再准备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对象,进入大队的领导班子。
这是典型的小溪积累成大河、将要冲向大海的标志:结合进大队领导班子的知识青年,是各级组织培养的重点苗子。一旦被培养,就有招工、招干、上大学、“农转非”的良机。
但是,任何好机会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就像河流在奔向大海的途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暗流险情。
我刚刚当了大队电工就撰写了几篇安全用电知识宣传稿件,在公社扩大站广播,被中宁县水电局长万光绪听到。他在全县安全用电大会上多次表扬,还给鸣沙大队专门批了三寸松木计划指标,鼓励打造水泥电线杆子,更换原来的木头电杆。第一次在鸣沙二队打造时需要懂行的人帮忙,以前的老电工倚老卖老地出现在打造水泥杆模型现场,阴阳怪气地说这不行那不行。中午二队队长安排一位农户家给我俩做了点米饭炒菜。那时候各队没有多少油水。农户做好米饭,滴了几滴香油,炒了点韭菜。端上桌子,炒韭菜的汤里漂浮着几点点油花花。老电工等农户刚刚离开就端起碟子,伸出舌头“刺溜”一声将油花花吸进嘴里。我恶心得只想呕吐。从此,一见老电工我就反胃。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喜怒不形于色”,内心的好恶他肯定知道,他开始不断在人前人后风言风语老说我骄傲自大。
那是1975年1月,我的心情和处境,再次像那美丽热乎的抛物线,瞬间结成了冰点:在大队待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叫人“搞”回了生产队。
一天早晨,当我手拿鞭杆、肩扛铁锹.正要到队上的饲养圈拉粪时,队长丁学文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说:“上面通知说,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叫你去一趟公社呢。”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县路线教育工作队来我们公社正在抓各种典型呢。他们叫我去,是否还因那篇小说呢?要真是那样,我这次去公社凶多吉少——

我在走进大队的前一天,大队的决策者们就安排我在全大队社员面前,作了一次面对面的批判发言。
一位在中学时拿钢鞭叫大队的决策略者身上开花(挨打)的知识青年回村后,老说自己的前途就像装进玻璃缸里的鱼——看起来四周光明,就是从哪个方位也蹦不出去,照片里的故事为题的作文。他实在不愿叫人家把自己当做熟烂了的牛皮,彻底毁在缸里,就偷偷外出搞了几天副业。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打了几天小工挣点小钱。这在当时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倾向。大队干部把他抓成搞资本主义倾向典型,但大会小会没人能说过他。大队干部说他一句,他可以说大队干部十句:大队某某干部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嫖、怎么赌,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搞得满场大笑。
有了七星渠工地上的表现,大队干部认为我是“笔杆子”,刚从马滩回来,支书就要我写批判那位知识青年的材料。我知道此兄不好对付,批判稿做了充分准备。
照片里的故事优秀作文1 我当我看见那张照片,我就会想起我家狗来。它叫棉花糖。它身披白大衣一双蓝宝石”眼睛,一双大耳朵,四肢灵活,毛摸起来很舒服。要说印象最深的事,那肯定是照片里的故事了。 星期六一大早。

我站在扎有红绸子的话筒前,一张照片的故事作文700字,发出的第一句吼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就是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
照片里的故事优秀作文1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爸爸、妈妈和我到了那里,哇,这里真是人间的天堂!到处五颜六色,山很高很高,远远望去,这些山奇形怪状,有像馒头的、有像狮子的、有像狂风卷起的浪花…… 突然,我有一个可怕的发现。
我没发言时,那位老兄还在人群中大声讲着大队哪个干部又在哪里胡吃乱喝的事实。我对着话筒一吼,他再也没敢出声。
发言到一半,大队书记叫几位背着钢枪的“武装民兵”把他押上了主席台——因我发言此兄被定为“敌人”。
我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他的头也就越来越低。

我就这样走进了大队部,虽说是先当了个大队电工,可不少人知道我下一步是要“进班子”的“青年干部”。
当时农村通电不久,农民还不懂得安全用电常识。加上经济条件所限,许多农民像通广播线路一样,找个铁丝就朝自己家里架通照明线,触电事故经常发生。大队开始配的电工不是大队干部的小舅子,就是大队干部的妹夫,二年级照片里的故事200字。

这些人本身没什么文化,跟着供电站抄表要钱的人跑了几天,带电作业、安全操作的本事学得很慢,吃卡要拿说断电就断电的恶习学得很快。只要谁给了好处,就可以不顾安全乱接电线。群众将当年的电工称作惹不起的“电老虎”。那个老电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我代替。
我清理线路时发现,个别大队领导家里用电不出钱:大白天老是开着几千瓦的大灯泡,还用自制的电炉子烧水做饭。公摊电费高得使有些农民家重新点起了煤油灯。
我当电工前,一根通有220伏电压的铁丝断在路边,电死了一个10岁小孩。

与一些大队干部们真正在一起接触后,发现有的干部真的就如那位我批判的老兄所说:吃喝嫖贿,样样俱全。
我陷入了难以应对的局面,就像正在朝前奔流冲击的河流,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险滩。
当时《宁夏文艺》(文学期刊《朔方》前身,创办于1958年)刊物刚刚复刊,我就以这些素材为例,写了篇小说寄了出去。万没想到:它带给我的却是——重回生产队,人生再次跌入低谷。此时,县上的路线教育工作队要我去公社。万一问起小说,我该怎么应对?

是去还是不去?
照片里的故事作文1 当时,是20xx年10月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才刚刚满6岁,刚上一年级,是国庆节的时候照的照片。 我们先从成都坐火车到广州再坐车到珠海,我们到了珠海已经晚上了,我们先去停车场停车,然后在去买海鲜。
眼看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最后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就走,到了他们面前我正好可以将这小说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他们敢抓我典型,我就将大队个别干部的实际作风彻底公开!已经把我从大队整回生产队,谁还能整掉我手中的锹把子?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来到公社,推开路线教育队员的房门。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干部从上到下将我打量了一番,问道:“你是……”
我作了自我介绍。
他又打量了我一番,问:“你会写小说?”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他果然打问的是小说!
他见我不说话,再问:“小说带来了吗?”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示意叫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说:“那你就先说说你那小说写的是什么吧。”
——是祸果然躲不过哪……
我就讲了下那篇小说的梗概:一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因表现突出被结合到了大队的领导班子,结果发现班子里有人被一个老光棍和一个年轻的寡妇拉下了水。
他问:“怎么拉下水的呢?”
我就绘声绘色地将那小说的每个细节讲了一遍,着重渲染了一番老光棍拉着马公子(种马)给发情的草驴(母驴)配种后,和前来找他的一个小寡妇在小屋子幽会,被大队长碰见了。大队长平时和老光棍一起在老光棍的小锅灶上用电炉子炖着吃大队里集体的羊肉。那老光棍反倒笑嘻嘻地将房门一反扣,将大队长和小寡妇关到了屋子里……

他边听边笑,最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扔给我说:“难怪区上要叫你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呢,你确实是个写小说的好料。
——真没想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下了一半,就对他说明了因这篇小说而给我带来的一些麻烦:小说寄出后,县上选拔我参加全区运动会。刊物编辑部将小说稿给我寄回来,要我按照他们提出的意见修改后再给他们寄去,并通知我准备参加全区文学创作学习班。复旦大学从1972年开始招收的“文学创作班”,就是从这样的学习班里物色学员。我的一位从小学念书到高中毕业,又一同回到大队的回乡知青同学,收走了我的信函。打开一看,如获至宝,改头换面地将小说的内容给大队的干部们念了又念,讲了又讲。
怎么样?听了照片里的故事,你一定和我一样,仿佛又回到了那快乐的情景中吧! 篇二:照片里的故事 翻开尘封已久的相册,记忆就像开了闸的河,顿时把我淹没在张张的记忆忆里。 相册里从我出生到现在,有几百张照片。

他急忙问:“结果呢?”
我说:“我的同学在3个月之内突击入党,取代了我原来的大队团支书,我在银川的田径跑道上还没比赛下来,就被大队干部辞回了生产队。现在正往地里送粪呢。拉马公子的老光棍到处放风说:‘杨森林这个生牛皮这回要在生产队的缸里熟烂了!”
中年干部一听,拍案而起:“这种的坏怂啥地方、啥时候都有呢!小说就是个小说么,怎么能与现实连在一起对号入座整人呢?你别怕,大队不留你,你来公社——我们现在正缺你这样能写材料的年轻人呢,照片里溢出的幸福作文七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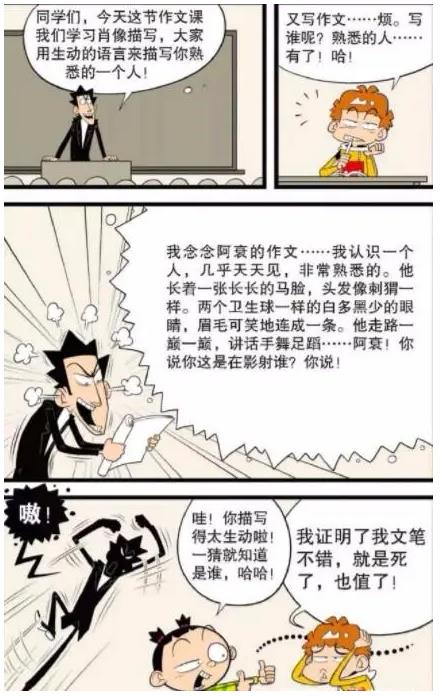
我从没想到的变化就这样开始了——
我堂而皇之地来到了公社,关于照片的作文700字,坐在了“路线教育办公室”,首先把辞我回生产队的大队干部吓了一跳。他们在我面前大骂我那位同学,说我的同学挑拨是非,借刀,目的是踢掉我以后,他自己想钻进大队领导班子。现在他们已发现上了当受了骗,不会叫他的目的得逞:大队团支书马上换人,大队班子的青年干部空位还给我留着。
我明白他们的用意,更明白自己的目标。
是夜,我来到塔河湾下的南河子边。南河子是黄河从南边方向流出的一条岔河,当时的河水流量与现在的黄河主河道流量差了不多少。
夜深无人。
照片里的故事作文 1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们的全家福。每当我看见它就激动不已。我不由想起那次愉快的旅行。 这张照片是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们一家人在雅安碧峰峡瀑布前照的。那天,我们从成都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碧峰峡。

河水哗哗作响,河面闪着银光。
我一边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面信步,一边对着河水反复念叨:“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江河,无以成大海。”
走累了,坐在河边反思我对那位先我一步“回乡知青”老兄的批判,再对比我这位同学对我的所为……尽管心中极为难受,但理智告诉我:彼时的我与此时的同学,动机与作法是否殊途同归?
人的成长积累到一定程度,到该转折的时候,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正是这一瞬间,相册里的什么作文700字,自己感觉一下长大了许多。
照片里的故事作文1 这张照片是我在悬羊岭照的,虽然这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背后却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故事的前景是爸爸的朋友与我们一家去悬羊岭爬山,当我们来到山脚下,虽然山的周围都被树挡住了,但是抬头一看这山——很高,呸!
自从在南河子边从心底谅解了那位同学,一下觉得自己像是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工作也就不用扬鞭自奋蹄了:白天,自觉到各队调研;夜晚,自个加班整理材料。
照片里的故事优秀作文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高处不胜寒……”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歌——《水调歌头》。 是啊,人生是迭宕起伏的,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大风大浪来阻挠你前进的脚步,但是我们不能伤心,不能失望。
我将整理过的材料交上面检查汇报以后,像在马滩时一样,按文体要求,修修改改,再寄出给《宁夏日报》与宁夏广播电台。与马滩时的不同是:《宁夏日报》刊登出来后,县广播站再采用时常常要在前面加一句:据《宁夏日报》某月某日报道。
每次有了这样的报道,中年干部就夸奖说:“对着呢——这就叫‘出口转内销’!”

“出口转内销”是当年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专门供出口的、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转向国内销售的特殊优质产品。中年干部还在县上抓此项工作的蹲点领导——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张居正面前夸奖我说:“这小伙子不仅有才,还有脑子!”
当时我并不明白他所说的“还有脑子”指的是什么。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县领导层内派别林立,与区上跟什么人、划哪派线极其严重。在我们公社抓点的张居正(后来他称我为“挚友”)如履薄冰,他抓的工作成绩通过省级媒体先报道出来,县广播站再以转载的形式广播,效果和策略是比较明知的。要是我给县广播站直接投稿,广播站反而为难,就是勉强播出了,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县领导张居正的赏识,自然在公社立住了脚跟。
翻开相册,我看到了六年级与同学们拍的毕业照。那时我们都不开心啊个个洋溢着欢乐的笑脸。看着相片,我的思想不觉得又回到了那个的时候。“来来来,同学们站好了,接下来该我们班拍照了。”老师看着我们欢笑。
为了帮我领到工资,中年干部与鸣沙公社革委会委员、水电专干杨凤朝,公社书记丁振民一起将我推荐为公社电工,同时兼任公社团委副书记,每月领到了42.5元工资外加2.5元劳动补贴。丁振民口口声声对人讲:“杨森林与喻通(后来是宁夏人大法制委正厅级主任)两个人我们当做干部使用!”
我与其他干部不同的是每月多2.5元劳动补贴——其他干部每月工资大都是42.5。
回乡时间2年后,我具备了推荐上大学的条件。县招办给我们公社分了两个上大学指标,其中一个是县上唯一的中文系。当时能上中文系学习就像如今能上美国哈佛耶鲁留学一样吃香。在那个“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特殊年代,文科——尤其是写文章搞创作的中文系,是当时上大学者的首选。
另一个指标,我活动着分到了我所在的鸣沙大队。尽管我同学被免除了大队团支书,只当了个生产队会计,可我还是帮他在公社主管招生工作领导———鸣沙公社副书记李天福(已经去世多年)跟前反复活动,最终一同上了大学。
照片里的故事优秀作文1 每看到我们家餐厅里挂着的那张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炎热的夏天 一天,我站在本垒上,手里拿着球棒,裁判一声喊:投球!对方的投球手把球飞速地扔过来了,我瞄准,挥棒,乒!球一下子飞到了场外。
当然在个人情感上少不了宣泄一番:我刚到公社时曾经做出过堂吉诃德般的荒唐“报复”——
我那同学与当时大队书记一个生产队,房连着房居住。我到公社调研时通过查他的会计账,发现他给大队书记和自己家多分了口粮。其他社员缺吃少穿,衣不遮体,长年累月很少见到荤腥,他家与大队书记家合砌的鸡舍,老远就能听到公鸡“沟沟欧——沟沟欧”地打鸣,母鸡“格格达——格格达”地叫蛋。我与当时最要好的结拜兄弟白天看准位置,待到夜深人静时摸到鸡舍跟前,抬起穿着部队军人当时才能穿上的大头皮鞋,对准鸡舍的土垡垃墙,几脚踹下去,墙就被踹开了大洞——手伸进去,朝鸡脖子一捏,鸡没有发出任何叫响,就塞进了身上的老皮大衣。待鸡塞好,再把土垡垃一一搬起来,塞严洞口。那时候卫宁平原上的农户家都是敞开着的院落,与今天欧美的家庭住房一样,很少有人家设围墙围栏。

我俩飞一般回到家,鸡在怀里就被捏断了气。开膛破肚后,放在铁锅里倒上水,架在电炉子上眼睛盯着往熟煮鸡。那鸡吃得很胖,不一会,翻滚的汤水里就漂出鸡身上朵朵油圈圈。我们一边急不可待地用铁勺撇着油圈圈抢着喝,一边大骂会计同学与大队党支书:这龟孙子给鸡喂的粮食,比分给社员吃的口粮都好——不然,这鸡怎么能吃得怎么肥哪?
大白天,我再次专门到他队上继续检查,还特地看了看鸡舍——洞口已经用带有麦草的泥重新泥结实了。
那时,我们白天装作是“天使”,晚上自诩是“侠客”。与几个最要好的回乡知青一起预谋计划着怎么偷最坏人家树上的梨、最霸道生产队长队上田里的瓜。三更半夜,相约跳进三四百米长、十几米深的大水坑,莽莽夜色中开始游泳比赛。同学张学胜有次差点出了爬不出水面深陷深水坑里游不出来的事故——现在见面相互谈起还心有余悸。为了培养各自的“侠客”胆识,每个人独自攀上夜晚人不敢去的鸣沙古塔,打开手电筒的光亮,报告自己已经爬上塔身。常常集中在鸣沙小学三个当民办教师的回乡知青——张学胜、张志华、毛建华宿舍,商议着怎么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谋划着各自的出路,探讨写作,大谈人生。
【篇一:照片里的故事】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在疗养院工作,他工作很忙,不能回家,我和妈妈就到疗养院去看他。那里环境很美丽,服务员姐姐也很漂亮,我非常喜欢。有一次,疗养院来了一位摄影师。
我当时的写作,今天看来只是些照猫画虎的涂鸦,而中年干部却一本正经告诫我:“写小说怕有人对号入座惹是生非,可以写其他文章,照片里的故事优秀作文。你的笔头子不错,人又有灵气,照片里的故事小标题形式,多多写。笔头子和那田里的犁铧子一样,越用越利索。千万不要成了老和尚的鸡鸡——越不用越退化!”

那时候,我们整天整夜聊天。正是与他的聊天中,我知道了“石空灯火”、“鸣沙过雁”、“余丁早春”、“牛首慈云”、“沙坡鸣钟”和《康熙访宁夏》。虽说他当时没个一官半职,可无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轻视他。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县上有名的笔杆子:他不仅公文材料写得出色,还发表过散文、小说和各种故事,是县上第一个出版过书籍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阎福寿——我们后来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后来我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工作时,为阎福寿和王非凡争取到了一笔出书补贴经费,帮助他俩出版了《杞乡传奇》一书。
2021、9、11于银川悦海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