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菊花

文丨了一容
在禾木河与喀纳斯河交汇的盆地里,马儿们在茂盛的草丛里吃得酣畅淋漓。可是,有十几匹不肯合群的马儿跑远了,已经瞧不见它们的身影。于是,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决定骑马去找回它们。
伊斯哈格一声呼哨,坐骑黑豹闻声而至,他腾空一跃,便跨上了马背,两只脚后跟在黑豹的肚子上轻轻一磕,黑豹立即小跑起来,伊斯哈格习惯性地挥动套马杆,“彻儿彻儿”地吼两声,并伴着双脚猛地连续夹击黑豹的肚子,黑豹立即脖子往前一抻,一道黑线猛地飙了出去,只听得耳边呼呼生风,辽阔的草原那一波接一波的草浪宛如翻滚的海水向他迎面扑来,最后伊斯哈格闭上眼睛,他感觉自己已经幻化成一绺黑色的豹子的毛在一片又一片的草叶上掠过。
牧马少年骑着这匹浑身乌黑如绸缎一样的骏马跑了很远,登上了一座山丘,又从山丘的那一端飞一般地驰下草坡,写一种花200字作文,终于远远地望见走失的那些马匹在茂盛的草海中时隐时现。

夏天到了,我家对面的土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可美了!放学回家,总有许多人在欣赏牵牛花。每天上学的时候,我总是先在家门口停下来欣赏下牵牛花,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上学。牵牛花的茎可重要了,没有它牵牛花就死了。
此时,香荫草的味道非常浓郁,浓得有些呛人,而野菊花的香味则在微风下淡淡地飘入人的鼻孔,进而沁人心脾。
伊斯哈格追上了走失的马匹,马儿们受到伊斯哈格套马杆的惊吓,左冲右突,但很快就被黑豹截住,汇聚到一起,朝着牧人驱赶的方向奔腾,轰隆隆,马蹄踩踏出动人心魄的声响叩击着喀纳斯牧野丰腴的胸膛,这诗意的乐章在中亚大地的上空久久回荡着。
日头特别毒,伊斯哈格经常会被晒得蛇蜕皮一样褪去脸上的皮。经历了毒日头,才能成为真正的草原汉子。草原上立着的,个个都是血性男儿,但他们浪漫起来比诗人都浪漫,太阳炙烤大地的时候,那些草原上雄鹰一样的男人们仿佛飞累了,就会躲在儿马的卵子遮挡住的阴凉下面喝起最烈的烈酒,喝醉了,就拔一撮骆驼蓬草苫在脸上,不一会儿便打起雷鸣般的呼噜。

少年伊斯哈格追回马群,他用双脚别在黑豹前腿的浅窝里,撕住鬃毛,嘴里发出长长的“吁”声,马儿便打起一个棱登,前半身腾空而起,双蹄在天上划拉出一道道弧线,随之轻轻地落下来稳稳立在草地上。他用手搭在眉际遮住刺眼的阳光,看到眼前的一条溪流如一条玉带子似的把草地从中间豁开了一条口子,这条闪闪发光的玉带子蜿蜒缠绕着飘向了喀纳斯河,河水欢腾着,浪花四溅地撵着跟禾木河汇合去了。
草原上的野菊花开得到处都是,这里一簇,那里几朵,白的、黄的,看上去清新可人又耀眼夺目,淡淡的香味使伊斯哈格想到了苦涩而美好的爱情,这两种色彩对比极其强烈的野菊花,释放出要么热烈迷人,要么淡雅端庄的草原风味。
伊斯哈格十一岁那年从外地来到了新疆的这片大草原上,这里的人不叫他的名字,却亲切地叫他河州鬼,说:“河州鬼,一挂式鬼得很嘛,那里的儿子娃娃,个个麻达(厉害)得不得了!”他知道,他的性格十分倔强,骨子里有一股子百折不挠的劲儿,一个人小小年纪能独自西行,到达几千公里以外的陌生世界,这种胆量也不是能够强装出来的,他天生喜欢骏马,他的血管里似乎流淌着一种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天性和基因,来到喀纳斯草原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弼马温”,他在马背上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骑马技术,尤其对野马充满了征服的激情和冲动,只要一爬上马背,他的身子就跟牢牢粘在马上一样,原本看着邋里邋遢、无精打采、鼻涕涎水的样子,裤裆还是拉在地上的,关于花的作文250字左右,但是一到了马背上之后,他突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显得英勇无比,人和马也仿佛化成了一个整体。他骑着马,如虎添翼,在草原上轻松自如地飞翔,那桀骜不驯的鹰隼一般的本色就会展现得淋漓尽致。
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早晨,我和妹妹一起去赏花.公园里的花真多啊!有月季花、杜鹃花、牵牛花…….各式各样.公园里的花真美啊!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白的似雪,粉的如霞,黄的似金,红的似火。
伊斯哈格就是喜欢这样骑着黑豹在草原上天马行空地驰骋,他喜欢无拘无束地在草原上自由翱翔,释放出百分之二百的人在城市里就会假装收敛的天性。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变得组织性和纪律性极强,无论是和伙伴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还是驯马、追马,他们互相会协作得十分默契,配合得天衣无缝,那种不谋而合的凝聚力会令旁观者不由自主地咋舌称赞。伊斯哈格第一次听着马的嘶叫,就觉得他和它们是那么亲切,就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弟兄,因此他就深深地恋上了草原,一心留在这里当一个合格的牧人。
伊斯哈格在喀纳斯草原阅尽了这里的四季风华。冬天的时候,喀纳斯河两岸彻底被冰雪覆盖,结冰的河水碧绿碧绿的,凝固后跟翡翠似的,那种美,会让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夏天,繁花三千,各种花草竞相角逐,大大小小的动物和昆虫们穿梭在花丛和草海里,尽情嬉戏和寻找各自的精彩与欢乐。一年一年,伊斯哈格看见喀纳斯河岸边的树越长越高,越长越壮,茂密着它们的茂密。花草也一茬接一茬地生长,在伊斯哈格眼里,这里的娃娃们也是一茬接着一茬,他们似乎不是女人们生出来的,而是从密密麻麻的草丛里面的花骨朵中生长和蹦出来的,一个个孩子跟哪叱似的,从一朵接一朵的野花的花苞里面一点一点长大,随着花苞的突然打开,一个小娃娃就这样从张开花瓣的花苞中手舞足蹈地蹦出来了,哇呀哇呀地喊叫着,惊动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动物们都跑过来,它们从绿色的海洋般的草浪中伸出脑袋,惊讶而快活地跳着舞迎接着新生命的到来。
牧野里的草,新的长出来之后,于是新的娃娃们也从花朵中生长出来了,他们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又站起来欢蹦乱跳的,吼一声就长大了,在草地上和牧野里奔跑、捉蝴蝶、撵野兔、摔跤、骑马、赶狼、驱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互相呼喊着对方的名字,那穿透力很强的野性的声音在中亚大地的上空回旋着,震撼人心。所以,喀纳斯草原从来都是一片欣欣向荣和生机勃勃的样子。
描写百合花的作文200字1 春天到了,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百合花也在暗中渐渐开放。还末开放的百合花胀鼓鼓的,开放时的百合花像一个个酒杯似的,大多数的百合花都有5~6个雌蕊和一个雄蕊。 百合花有的是粉红色的。

”“满树金黄细小的花儿,点缀着红叶娇艳的季节。更有那浓郁的芳香,‘一味恼人香’袭人心怀,沁人肺腑。又在芳香中带有一丝甜意,使人久闻不厌。”……好美的语句,好美的花,文章对桂花的描写是那样的神奇。
牧马少年伊斯哈格骑着黑豹跟四五个牧马的伙伴越过了哗啦啦欢叫着的喀纳斯河,进入对岸的深草中,马儿们在盆地里安心贪婪地吃着青草,有些青草不小心伸进马儿们的鼻孔,使得它们的鼻子里像是有一群小虫子爬进去,痒痒得难受,便秃噜秃噜地打起响鼻。
一群牧马少年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簸箕形状的土崖,在下面开始挖灶升锅,准备野炊了。他们从早晨出来,已经过了晌午了,还没有吃任何东西,肚子早已经饿得跟癞蛤蟆钻进去了一样,呱呱呱地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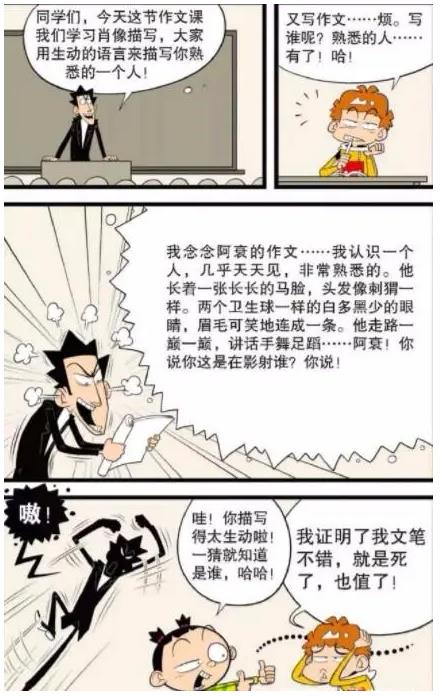
努努是他们当中的大娃娃头儿,他提着放牧牲口和羊群时常带在身边的剁铲,倚着簸箕形的崖面子下面铲出了一个锅灶的平台,然后挖好安置铁锅的灶台,再把烧火的灶门捅开,拱形的灶门显出结实的承受力,当然这样的灶门生起火来之后,火不仅旺,火头还会直奔锅底强劲舔舐。这一点,努努是非常有经验的,剁铲于他可谓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无论是剁还是铲,都张扬着他那粗粝本真的个性。努努手里的这把剁铲,有一根一米多长的结实的木把儿,牧人带着它在身边,用途可谓广泛至极,它可以铲开荆棘泥泞,也可以给打滑的道路取土铺路,它的头就是一把给粮食除草铲子的模样,有些牧人用它随手抄起泥土扔出去能打得很远、很准,起到拦挡马匹和牛羊的作用,有些会在它的木把上系上一根尼龙绳子,挽在胳膊腕子上,避免丢失。
此时,努努为他刚刚挖好的锅灶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在上面用巴掌拍拍打打地欣赏着,不停地修饰着灶膛,把里面收拾得光光堂堂的,写花的小练笔200字左右,并用手试探着里面的光洁平整。忙完了这个,努努劳苦功高地坐下来休息了,他对一旁赞美着他的杰作的伊斯哈格几个伙伴命令,“你们还不赶紧找柴禾去,愣在这里干啥呢?”他揩了一下鼻子上的汗珠子,说,“我的锅灶挖成了,现在,我要好好休息一会儿,等你们的柴火找回来了,我再给咱们做饭!”
于是,伊斯哈格带着拉西、尔里,还有尤布和阿依努尔,沿着喀纳斯河左岸的上游走去。阿依努尔是一位美丽大方,且有些活泼开朗的少女,大家都叫她野菊花。有些人把野菊花当成了格桑花,也有的误认为它就是大波斯菊,抑或翠珠、洋甘菊、幸福花。实际上,野菊花就是野菊花,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野菊花个头要小一些,只有在草原上长期生活过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就像有些人把草原上的臊胡子当作野葱,尽管它们都有一丝辣味,但野葱的葱管要粗要圆一些,臊胡子要细小一些,而且臊胡子的株筒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它们长得就像一对孪生姐妹,都是一撮一撮地生长,牛羊特别喜欢吃它们,而马并不喜欢吃这种植物。阿依努尔太喜欢野菊花了,她的头发畔畔上经常插着几朵野菊花,她本人看着更像是一朵美丽多情而又热烈绽放的野菊花。
他们嘻嘻哈哈向前奔跑起来,惊动了吃草的马儿,马儿们抬起头,昂着披挂着秀鬃的优美的脖子,向前耸立起耳朵,好奇地看着他们。
大家走到一片乔木和灌木接连和纵深的地方,大树上缠绕着许多老藤枯蔓,林边的土道上有牧马人骑着烈马扬尘而过的身影。这片乔木粗壮的草地上,总有冬天被暴风雪折断的老树棵杈,经过一季一季夏日太阳的照晒,完全干透膛了,表面都皴裂了,轻轻一折就断成截,这是烧饭最好的柴禾,大家边走边捡拾着柴禾。阿依努尔抱不动粗壮的木柴,大家都特别呵护和包容她,让她找点干死的牧草和灌木拿回去,作火引子就可以了。
描写夏天荷花的作文200字1:夏日荷花池 夏天,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到老家的莲池边散步,晒晒太阳。老家的荷花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我来到荷花池边,过来时远远看见荷花池中一片碧绿加上隐隐约约的粉点。

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大片牧草深可齐腰的深草丛中,牧草浪绳一样浪得人的腿都迈不开。大家就在草里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些牧草简直茂盛齐茬得就跟人工种植的苜蓿一样,微风过境,牧草的腰身便齐齐地弯下去,随之又挺直了,接着又一次轻轻地弯下去,一起一伏间,相互碰撞磨擦,发出“唰啊、唰啊”的声音,犹如大海的波涛缓缓地涌过来,一次一次拍击着沙滩,发出低低的涛声与吟唱似的。
突然,不知道是拉西还是尔里喊了一声:“快看,野兔、野兔!”大家都围拢过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正当大家要责备他大惊小怪的时候,一只小小的野兔从他们的脚底下跑了过去,看来这只小兔子出生时间不长,看见人来了还不知道躲藏起来,倘若是成年的野兔,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柴禾,不约而同地商量着要抓住这只小兔子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大家确立了范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围圈,开始收缩包围圈了。尤布一边包抄,一边兴奋得吱哩哇啦地喊叫着。
阿依努尔噘起小嘴,假装生气,对他说:“小声点,别嚷嚷,你这个讨厌鬼,把小兔子都吓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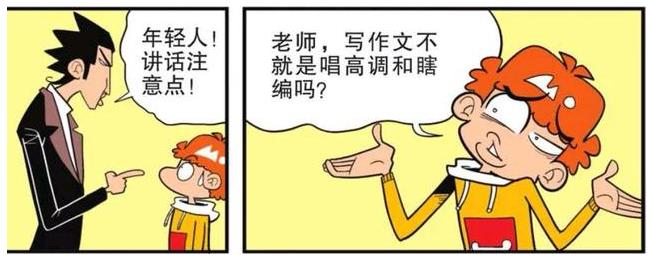
大家只好蹑手蹑脚地向前推进。小兔子就在大家形成的包围圈里,因为这里有野兔的明窝,野兔的暗穴是比较深的,而这种明窝不会被狐狸和狼堵在里面,容易转移和逃跑。狐狸和狼是野兔的克星,它们是草原上的气功大师,把野兔堵在窝里以后,先是用爪子刨开一截洞穴,剩下的部分,它们不会再费劲巴拉用那么大的力气挖到底的,而是像吹气球一样鼓着腮帮子往洞穴里吹气,直到洞穴里灌满了气,野兔在里面被胀得晕头转向,受不了了,便不顾一切地爬出来,刁钻而狡猾的狼和狐狸便把野兔一口叼住,就这样兔子成了它们的一顿美餐。
伊斯哈格一个虎扑抓住了小兔子,揪着它的一对小耳朵,把它从草丛里提溜出来,小兔子拼命蹬着腿,大家都惊喜得跳起来,争先恐后地用手摸着毛茸茸的小兔子,它身上的皮毛那么光滑细腻。阿依努尔从伊斯哈格的手里接过了小兔子,爱怜地捧在怀里,抚摸着它身上的纤柔的细毛毛。
尔里说:“是不是已经长到吃肉的时节了?如果能吃肉,咱们就宰了吃了去!”
拉西说:“现在还没有长大,咱们抓回家去,把它养大了再吃它。”尔里也比较赞同,关于花的作文100字,说是现在太小了,还不够吃一顿的。
大家的话让阿依努尔心里特别难过,她眼里噙着泪花,不让他们再用手接触小兔子,她说:“我们带走小兔子,小兔子的阿帕(妈妈)回来找不见它,该有多么难过呀!”
听了阿依努尔的话,伊斯哈格建议大家摸摸抱抱小兔子,把它放了算了,让它去找阿帕(妈妈)去。
我喜欢花,喜爱她们或娇弱或富贵,或朴素或充满激情的颜色,因为这就代表了她们——开得无声无息却生命力惊人。一朵花,或许在你眼中微不足道,但我坚信,她的存在自有她的价值与使命。春天,花儿还未开放。
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由阿依努尔把小兔子亲自放回野兔的明窝旁边,野兔子的窝上面被一大丛灌木遮掩着,窝里面由于兔子经常出没和卧着休息,已然蹭得油光光的,还有几撮兔毛挂在窝门口的刺枝上轻轻地飘拂着。
放了小兔子,大家回身拿了柴禾,走出不远,阿依努尔却有些不放心,说:“我回去再看一看小兔子还在不在?”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说赶紧回去做饭,都饿得肠子粘贴到脊背上了。但是阿依努尔还是坚持要去一探究竟。结果,她走错了路,进入了一片陌生的林草带,远远地听见阿依努尔发出一声惨叫,大家闻声放下柴禾飞奔过去,原来是一条大长虫咬了阿依努尔的腿。一些牧人经常说,如果自己被长虫咬了,你抓住长虫把它再咬一口,人就会平安无事的。他们留下尔里照看阿依努尔,描写花的日记200字左右,其余的人都追着抓长虫,这条长虫浑身光可鉴人,精气神很足,拉西用土坷垃砸过去,它竟然跃起一人多高,在空中摇摆扭曲着乌黑有力的身子,就像一条鳗鱼从天而降,它滑跌进草丛中。拉西和尔里对这条充满力量的大长虫开始有些畏惧,但长虫却激怒了伊斯哈格,为了阿依努尔一定得把这个坏家伙抓回去,另外他还担心刚刚被阿依努尔放掉的小兔子就在附近不远处,被长虫找到吃掉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伊斯哈格脱掉了身上的白汗衫,循着大长虫的踪迹尾随追赶。长虫在草上,就像鱼在水中,它会玩它的草上飞。但是伊斯哈格从来不怕狼虫虎豹。据说,人的基因里面有许多惧怕野兽和蟒蛇的因子,有的人老虎豹子都不怕,但天生就怕长虫,看见这个浑身光滑冰冷阴森森的家伙,写一个花的作文300字,全身就会不寒而栗。但是伊斯哈格好像基因里没有这个概念,他闪躲腾挪,猿人一般,几个纵步就追上了大长虫,他瞅准时机,一个乌龙探海,飞身过去用衣服压住大长虫的上半部分,摸到并抓住了长虫的七寸,他摁住它的脖颈,从紧连着头部的后脖颈把它提溜起来,另一只手抓住蛇的身子。他牢牢地控制住了大长虫,长虫的头部从衣服下面露出来,一对阴森森的令人恐怖发寒的眼睛仿佛是要把他们深深地记在心里,那个长虫的芯子心有不甘地扑簌簌扑簌簌出出进进地在嘴边缭绕着。
他们一边向阿依努尔身边走,一边寻找长虫的克星一字蒿,这种蒿草只要嚼烂敷在长虫咬的伤口上,很快就能治愈伤者。也许世上任何病菌都一定会有一种化解和对付它的植物,也许是某类蔬菜或野草什么的,只是人类认知有限,没有发现而已,这就是绿色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悲悯之情和无偿馈赠吧。

阿依努尔被长虫咬过的地方,流出一丝黑色的血液,但那一块地方开始发黑变肿了,情况紧急。大家让她把抓到的长虫狠狠咬一口,阿依努尔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感到恶心,摇着头不肯咬,牧人们讲被长虫咬过的人反过来再咬了长虫,人口里和牙齿上的毒就会重新进入到长虫的身体里,这样人自己就能活下来,长虫就死了。眼看阿依努尔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紧张使她的呼吸更加急促,美丽的脸颊渗出细微的汗粒,汗粒在细细的汗毛上游荡着。
大长虫在伊斯哈格的手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好像是在对他们示威。伊斯哈格有些愤怒了,抡起大长虫甩鞭子一样抽打着身边的草地,一连几下,草被抽倒了一片,大长虫的筋骨都散了,脑袋砸在柴禾棍子上,碎裂开来,再也耀武扬威不起来了。伊斯哈格丢下奄奄一息的大长虫,又跑去找一字蒿,他知道一字蒿的生活习性,找了几圈就找到了,放到嘴里咀嚼着,飞跑回来,嚼烂的一字蒿碎末和着他的唾液一起涂抹在阿依努尔的伤口上,他又用几片树叶包在伤口上面,用草绳绑住。伊斯哈格背着阿依努尔,他感到她的身体热热的如一团软绵绵的火焰在灼烫着他的脊背。他们几个抱着柴禾,拖着死长虫回到了要造饭的簸箕崖那里。
努努听了他们寻柴禾的经历,表扬了伊斯哈格,草原上对临危不惧的英雄向来是十分崇尚的,努努看着背回阿依努尔的伊斯哈格,说:“你嘛,真是一个勇敢的巴郎子,现在你和阿依努尔休息,我们几个做饭。”
早上从驻地的帐篷出发的时候,大家都各有分工,谁带小钢盅锅及切菜板,谁带米和土豆,谁带葱和清油、食盐什么的,分配都是非常明确的。伊斯哈格坐在簸箕崖下面距离锅灶不远的草地上,悉心地照料和守护着阿依努尔,阿依努尔的头枕在伊斯哈格的大腿上静静地休息,土崖就像一把伞盖,遮住了这中亚大地头顶上灼热炙烤的烈日,使他们生火造饭的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有阴凉的犄角旮旯。

拉西和尔里拿着阿依努尔从家里带来的瓦罐去河边打水。水打来了,他们用头顶着打满水的瓦罐回来了。这里的人习惯用头顶着盘子、罐子、笼子,顶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行走在草原上。努努让尔里淘米,让尤布和拉西把粗长的柴禾折断弄短,便于塞入灶膛。这个簸箕崖下面,四面遮风,非常僻静,是生火造饭的绝佳位置。
喇叭花也是好花,它早开晚败,它和太阳花似乎是一对好姐妹,它们约定好了一起开放、一起进入甜美的梦乡,从不早开、早败,一起装点着这美丽的大自然。它们无私的奉献自己,从不要求祖国的回报和人们的赞赏 太阳花虽然没有玫瑰的高贵。
伊斯哈格看见阿依努尔的头颅侧着,枕在他的腿上安静地看着努努他们生火造饭,他盯着她头发上插着的两枚黄色的热烈的野菊花,那头发就像是一片茂密的牧草,而那牧草上似乎开放着火焰一样燃烧的野菊花。这些牧马的少年,每天所接触的,唯有这样一派苍茫高远的大草原,抬头是浑然的天,低头是浩然的草。伊斯哈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听着阿依努尔这朵野菊花枕着他的腿均匀安详地呼吸,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和放松……远处,牧野里的草如海浪一样翻滚着,一波接一波,起起伏伏,盈亏循环,听上去如同置身于涛声连绵的大海边。他感觉阿依努尔也像是和他一样在静静地倾听,有时候牧草的声音听着就像是特别遥远,然而又似乎近在咫尺,渐渐会出现一些幻觉,仿佛草原上一切绿色的草木都在人的耳边喃喃絮语;蜜蜂在各种各样的花丛中飞来飞去,演奏着亘古的合唱;蝴蝶成群结队地去那草地上翡翠一样迸溅着的溪流边饮水,密密麻麻抱在一起,犹如人类去往圣地朝觐一样。这是草原上另外的一种宁静,是中亚大地上真正独有的一种风景。叫蚂蚱曼妙的叫声在簸箕崖顶的香荫草丛中奏响,絮絮叨叨的,催眠曲似的,这些让阿依努尔枕着伊斯哈格的腿昏昏欲睡。不知道是阿依努尔的鼻息还是她头上的野菊花发出一丝隐隐约约的香味,这是伊斯哈格感受到的最原始最古老最朦胧的一种幸福,这种感觉单纯而甜蜜,美好充斥着他的内心世界,他担心这温馨会稍纵即逝。但至少此时此刻,他却耽于香馨里,是实实在在的,草原上的一切在他的心里填充得满满当当的。

木棉花又开 我静静地走在幽静的小路上,享受清风拂过脸颊.一朵木棉花从空中飘落,我俯下身,认真的看着这朵如火焰般美丽的花,心中感慨万千……现在我很少能在街道上看见木棉树,他不像普通树木那样枝叶繁茂,可以遮挡刺眼的阳光。
锅热了,清油倒进锅里,刺啦啦地炼出一声响,然后就放入食盐,再将切碎的浓葱和野葱一起放入,接下来才将切好的土豆倒进去炒得半生不熟,这样炒得夹生的土豆入味好,熟得慢一些,最后才将洗好的大米和小米混合倒入锅中跟土豆搅拌一下,倒上水,水要将米淹过一些,然后盖好锅盖把米饭和土豆一起慢慢蒸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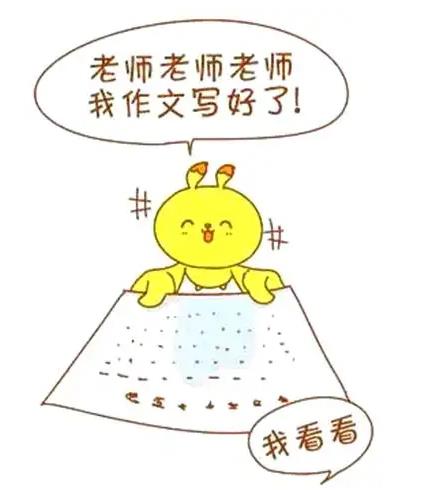
蒸米饭的时候,大家议论起了这条咬了阿依努尔的死长虫。“把它带回去,装到瓶子里晒成蛇油膏,谁要是身上起了毒疮,抹上立马就治好了!”尔里说。
尤布附和说:“对,没错,这个季节,它会成为最好的蛇油膏!”
努努反驳他们说:“它的肚子里说不定吃了什么小动物,要把内脏清理掉,用长虫皮制作疮膏,长虫肉咱们吃了,那可是最有营养的!”他说着又吸鼻涕又咂嘴,好像他已经吃到嘴里似的。
尤布说:“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尔里也说:“听老牧人讲,长虫肉是上好的补品,吃了长虫肉,即使身体非常虚弱的人也能缓过来,全身都生劲儿。”
“那就让刚刚被长虫咬过的阿依努尔也吃点长虫肉补一补吧!”沉默了半天的伊斯哈格丢了这么一句,接着又看阿依努尔头上的野菊花去了。阿依努尔一声不吭,看样子很疲倦,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好像是表示她不要吃长虫肉。
努努把长虫头用剁铲截掉,把蛇的尾巴那部分也剁了,因为有些长虫的毒就在尾巴那一段,所以是不能吃的。努努一边干一边说:“我见过长虫吸鸟雀,你们谁见过吗?”
月季花的颜色真多:有深红的,有粉红的,有玫瑰红的,还有橘黄和银白色的.那花儿有的盛开着,张开了一张张笑脸,有的才长出两三片花瓣,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只是个花骨朵儿。一阵风吹来,月季花散发出阵阵清香。
尔里说,他见过,实际上他并没有见过。尤布发自肺腑地说,他确实没有见过,只是听草原上的人们讲过,让努努讲给大家听。

努努:“长虫往往先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凑近了小鸟,然后会迅速把前半截身子像棍子一样直立起来,头对着小鸟,嘴巴咝咝地吐着芯子,跟火苗似的,然后鼓着全身的劲儿开始用嘴对准小鸟隔空发力,像是在作法术。非常神奇,再看那鸟雀,翅膀‘啪啦、啪啦’地拍打着,翅膀尽管扇圆了想飞起来,可无论怎么努力和挣扎,张开的翅膀依旧拖拉在地上,飞不起来,有些鸟雀眼看就要飞起来了,却又被长虫吸下来掉在地上,最后身不由己,身子竟然一点一点移到长虫的嘴边,这时,长虫前半截身子就会弹簧一样唰地一下子弹射出去,一口就将鸟雀吞进肚子里去了。”他接着说,“在夏伏天气,长虫是最厉害的,这时候如果人被长虫咬了,倘若在短时间内没有救治的好办法,拖延得久一点儿,那可就危险啦。但过了伏天季节,蛇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就变乏了。”他说,“我们家以前有一头红公牛,在伏天的时候,吸了一条长虫,哎呀,自从吸食了那条长虫之后,变得那个膘肥体壮,全喀纳斯草原的牛都打不过我家的这头公牛了,就是因为它吸食了一条大长虫。”
伊斯哈格看见阿依努尔睁大了眼睛,那绒绒的眼睫毛上下翕动着,似乎在出神地倾听着。
拉西说:“我也见过牛吸长虫,吸的时候,牛的头会深深地低下去,埋伏着似的,尾巴夹在屁股的沟壕里,前面的蹄子刨着地上的土,描写花的作文200字三年级,刨得尘土飞扬,那一阵牛身子会拱成一张绷得很紧很紧的弓,浑身每一根毛都仿佛绷着劲儿,鼻孔突然变粗,嘴里好像还挣得泛着白沫子,那力量,简直用圆了哩。这时候,人可千万不能打扰和惊动了牛,人如果惊动了牛,牛的注意力一旦分散后,就跟法散了一样,让长虫逃之夭夭了,从此受过严重打击和挫败的牛就会瘦成干棍棍,光拉稀,再就一蹶不振,缓不过神气来了!”
努努说:“长虫被牛吸到嘴跟前,牛会鼓着一口仙气,嚎叫一声,从鼻子上吸长面条一样吸进去,吸了长虫的牛,过不了几天,就缓好了,精气神焕然一新,就跟脱胎换骨了一般,身上的毛闪闪发亮,好看得跟缎子被面一样,光滑得苍蝇都趴不住。”
它在与严寒风雪做斗争中怒放着自己的美丽,默默地散发着醉人的香味。没有蝴蝶相伴,没有蜜蜂光顾,甚至没有绿叶的衬托。站在花树下,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王安石写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灶膛里丢入各种干透的枯树枝和用脚踩断的劈柴,开始燃烧得异常欢实,火苗扑燎燎、扑燎燎地舞动着,一会儿又呼啦啦、呼啦啦嚣叫着,同时柴棍子被烧得哔哔剥剥炸裂开来,一个劲儿地脆响着,那些烧化了的木棒,先是冒着乌烟慢慢弯曲收缩了,最后又由红慢慢变黑了,彻底燃过以后就变白了,成了白色的灰烬,释放出淡蓝色的白烟,闻上去香香的。木质的香味和饭菜的香味同时在草原的周围四散弥漫开来,让人心情愉悦和精神陶醉。伊斯哈格的胃也开始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欢叫和歌唱。
说着话的当儿,努努又把大长虫的肚子豁开,把里面的内脏,从头到尾用剁铲刮得干干净净的,果然从长虫的肚子里刮出了几只整只的小鸟,就像包了一层胎衣一样,然后努努有些气愤地把长虫皮一抹到底,完完整整从长虫身上扯了下来,剩下的就是长虫肉了,他让尤布帮忙倒出罐子里的水,把长虫肉洗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从灶火门里拨拉出两根烈烈燃烧的火棍,用一根木棍扎住长虫肉,放在这拨拉出来的火上烤,一边烤一边往长虫肉上洒盐,长虫肉被烧得蜷缩了,肉也瞬间变少了,肉上的长虫油吱吱叫着,散出让所有的人都精神为之振奋的香味。长虫肉不能烤得太久,因为肉薄而嫩,非常容易熟。努努给大家一人撕了一截,请大家品尝。但是,阿依努尔却只是闻了一下,皱皱眉头,又摇摇头,把它递给了伊斯哈格,叫他替她吃了。伊斯哈格和努努他们都劝说阿依努尔,长虫肉是大补,刚才被大长虫咬伤,又受了惊吓,身体虚弱,吃点长虫肉恢复得快。但是阿依努尔还是拒绝了大家的好意,不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还是嫌弃它的肉不干净,反正她就是不要吃长虫肉。

大家就不再劝说,各自吃得开心自在,吃了长虫肉的草原上的这些儿子娃娃们,感到筋骨里面开始发热和充满一股无穷的力量。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这大草原的环境所缔造出来的主人,就是这片绿色的大海一般的草原法则和秩序的维护者,草原和大海一样,有时候温情脉脉,有时候又会张牙舞爪,露出狰狞的面目,大海有怒涛和鲨鱼,草原有凶残的野兽,也有山洪和暴风雪,适者生存,你没有能力去适应,那就只有被淘汰,一切生命都是由大自然来塑造的,绿色的大草原让这些儿子娃娃们变得天然而质朴,桀骜不驯又阳刚强悍。
草原上的人都能歌善舞。阿依努尔简直就是跳舞的精灵,从小就跳得有板有眼的,她一跳就会跳出一种高傲和挺拔的精神和感觉,立着腰身,昂首挺胸, 头部、颈项、手腕,还有眼睛、肚脐,每一个部位都在舞着蹈着,时而骑马,时而剪羊毛,时而挤马奶,各种的造型和旋转,黑走马和哈熊也交替出现,插在她头发上的野菊花仿佛洒脱自如地流淌着草原人民的生活气息。
但是,遗憾的是伊斯哈格他们现在欣赏不到阿依努尔的舞姿了。
长虫肉并没有解决大家的饥饿问题,只像是饭前的一丝干果和小点心,反而勾引得大家更饿了,差点等不到米饭熟了。努努在地上插着剁铲,看着那剁铲木把的影子的移动,终于走到了他画线的地方,就开锅舀饭了。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洋铁碗,折几根柠条当筷子。这种野炊的饭菜,再就一点野葱,味道好极了。阿依努尔让给她少舀半碗,她爬起来靠着伊斯哈格,吃了多半碗。大家都是抢着吃,努努是最有经验的,第一碗他先是给大家舀得多,给自己舀得少,所以第一碗他很快就吃完了,第二碗他给自己舀得特别满,剩下的大家一人只能再少分一点,因此努努比大家都吃得多,占的便宜都大,但是大家也不去计较,毕竟人家年龄要大一些,个头也高一些,关键人家是厨师,近水楼台先得月,窝门前的雀儿先大,就是这么个道理。总之,不论是谁,大家都先紧着阿依努尔,让她先吃饱,但是她说她已经吃饱了。饭虽然被大家一哄而上,争着抢着吃光了,但肚子似乎还意犹未尽。饭后,大家开始仔细认真地把火统统用土掩埋了,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火星子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又用脚把掩埋火星子的覆土踩结实了,连整个锅灶都被壅进了土里,这是草原上生活的常识。
等到天黑的时候,马儿们一个个肚子吃得端溜溜扎起来了。牧马的伙伴们,嘴里唱出一句:“肚子吃得端溜扎,唱一个刘三姐她妈妈。”这句话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有一次草原上放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刘三姐》,二年级写话的小作文250字,第二天大家在牧马的时候,因为这个盆湾里草太好了,马儿们吃得肚子都鼓鼓的,又喝了喀纳斯河里的矿泉水,就跟怀上小马驹似的凸起来,尔里这个卷毛头就快乐得跳蹦子,嘴里哇啦哇啦喊叫着说:“肚子吃得端溜扎,唱一个刘三姐她妈妈。”伊斯哈格没有弄明白,他怎么这么激动和亢奋,为什么不唱刘三姐,却要唱刘三姐她妈妈呢?于是,一个传一个,牧马的少年们每次在打马回家的时候都这样说,就跟开心过头控制不住嘴巴,要给草原唱一个大肥喏似的,以表谢意。
马儿们还在克噌克噌地咀嚼着青草,把自己的嘴巴和头颅都淹没在青草里,并轻轻地愉悦地打着响鼻。
日头搭在草原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变得红红的,像一滴红色的泪珠,大家都开始汇集马群。这片巨大的草原上,野生动物特别多,有雪豹、貂熊、紫貂、北山羊、黑獾,还有驼鹿、棕熊、雪兔等等,不计其数,有时候狼群、雪豹和熊会攻击落单的马匹。但不管是多么凶残的动物,它们毕竟都是躲着人类的,有些记忆会刻在它们的血液和基因里,就像老鼠躲着猫走一样,魂仿佛被吸了似的。据说在非洲的草原上,有一种原住民,草原和森林之王狮子看见他们披着红斗篷追过来,就没命地逃跑,生怕腿不够用似的。所以,那里的小孩子的成人礼就是去到草原上独自征服一头狮子,证明他真的长大了。
伊斯哈格把阿依努尔拽上他的马背,让她抱着他的腰,黑豹咴儿咴儿轻轻地叫着,懂事地驮着他们稳稳地走。大家都骑上了马,循着夕阳红彤彤的足迹赶着马群往村子里走。一路上,马群踩踏出的声音雄劲而有力,就像洪流一样。所经过的木屋和毡房在夕阳的辉映下,炊烟袅袅,有着令人叹息的美丽,村落与青草河流小桥完美交融,空谷幽远,清净而远离人类的喧嚣。

从此,伊斯哈格在喀纳斯的草原上就这样走来走去。当他每次赶着马群回到村子的驻地的时候,他就听见村子里的人在悄声议论:“我们这次找到了一个有责任心喜欢草原和很会放马的巴郎子。他虽然是从外地来的,却并不是一个胡日鬼,而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好娃娃。”伊斯哈格听了这话,便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不免有些找到位置的尊严和自豪感。于是,他每天一大早,就会赶着马群去草原上了,他会找最好的牧草让马儿们吃得饱饱的,吃得心花怒放,一匹匹都膘肥体壮,他才会心中充满快乐。他对草原之外的世界已经忘记了,感到淡漠了,他完全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他能和野菊花阿依努尔一起放马,能常常在草原上见到野菊花。
但是,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生离死别组成的,夫妻两个在一起摸爬滚打一辈子,也还是免不了要分离,就像许多书和影视里描述的那些义结金兰的兄弟姊妹说什么“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每个人都是各有各的归宿,各走各的生死路。又过了两年,阿依努尔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被亲戚介绍给了布尔津木器社的一位大个子的木匠做了妻子。结婚的前一天,阿依努尔赶着她家的马匹到草原上让伊斯哈格放牧,说:“我家的马匹以后就交给你牧放了,我要到布尔津去了,以后你来布尔津时我招待你。”伊斯哈格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心情沉重地点点头。她回去时,要骑她常骑的那匹枣红马,可是那马要撵马群,独自怎么都不肯回去,挨了一鞭子,竟然尥起蹶子,差点把阿依努尔摔下来,吓得她脸都红了,头上插的野菊花掉到地上的草丛里,被马蹄踩踏后,变得面目全非。
伊斯哈格让她放开枣红马让它回到马群,他打了一个呼哨,黑豹一声嘶鸣,从草丛里跃出来,他骑上黑豹,把阿依努尔拽上马背,让她在身后抱着他的腰。这一幕,是那么熟悉而又久远。他打马向村子里飞奔,亲自送阿依努尔准备明天的婚礼。快到村口的时候,他感到阿依努尔的脸庞贴着他脊背的那一片变得湿漉漉的,一开始他以为那是捂热以后的汗水把后背濡湿了。他放下阿依努尔到马下的时候,看见她的一双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的样子。她的确在他的背后偷偷地哭了。她挥手说:“明天的婚礼,你一定要来啊!”

第二天,他把马群赶到牧草最深的峡谷里,他没有回去参加阿依努尔的婚礼,他想那一定非常热闹。下午的时候,他想着阿依努尔此刻一定已经坐着古老的马车,按照当地的风俗走了。
伊斯哈格突然乏乏地躺在深深的牧草里,觉得整个草原空荡荡的,一切都是空的,心也是空的。他辗转反侧,猛然坐起来,突然,他看见了一簇簇草原上的野菊花,它们依旧开得灿烂,黄色的,像火焰一样在燃烧,而白色的,依然恬静端庄,优雅高贵。

了一容,东乡族,本名张根粹,出生于宁夏西海固,一级作家。小说曾获中国第三届春天文学奖、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十年《飞天》文学奖、十五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奖等奖项。作品曾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出版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玉狮子》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