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贵州大曲”以“记忆里的味道”为主题,面向全国开启征文活动,共同挖掘每个人记忆里的故事,寻找品牌与国家共同成长进步的力量。即日起,茅台时空将转载“记忆里的味道”征文活动中获奖的优秀稿件,与读者们再次品味生命里的美好瞬间。
今天推出的是特等奖作品《故乡的大头青》,作者朱学东是前媒体人,书评美食美酒专栏作者。
故乡的大头青
春节,就是每年的第一天,家乡人叫大年初一。大年初一这天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除旧迎新。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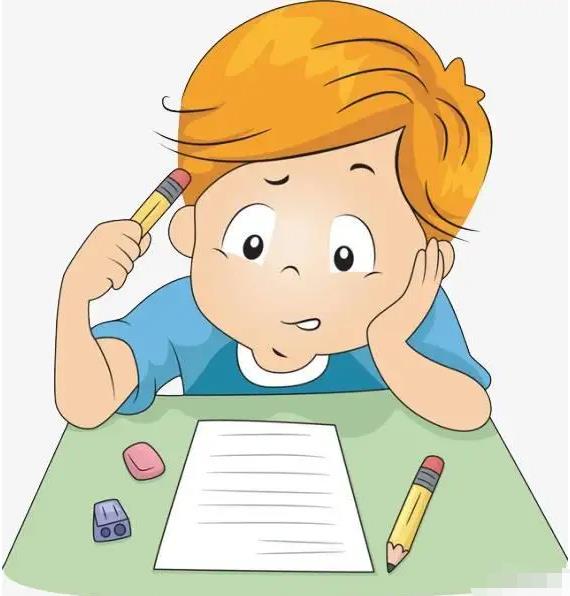
在故乡所有的吃食中,我最惦记的,是故乡冬日的青菜。
故乡在江南,江河湖鲜,时令疏菜,名动天下者颇多,按说,怎么也轮不到一棵不起眼的冬日青菜,让我念兹在兹,从前美食名家如倪云林李渔袁枚等,更不会将这样一棵青菜放在眼里。
但我惦记冬日故乡的那棵青菜。
客寓北京三十六年了,每到深秋霜降,我总是会不争气地想念故乡的青菜,而且年岁愈长,念想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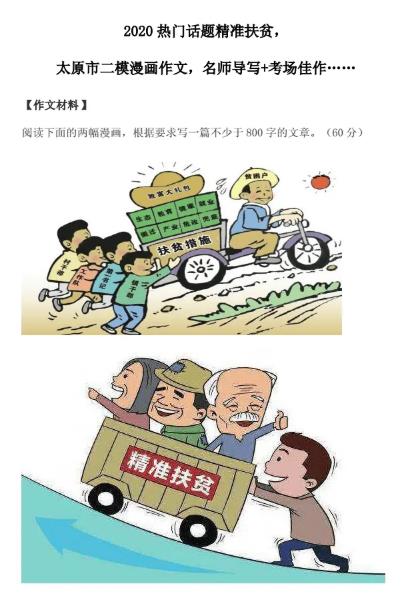
八蒜。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是传统的“小年”。这天,人们要把灶台打扫干净,杀鸡宰鸭来祭“灶神”。腊月二十五日前后,人们选择吉日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迎新年。这时,千家万户都忙碌起来,买菜,割肉。
故乡有两季青菜,一种是夏季青菜,就是如今流行的小青菜、鸡毛菜一类。
夏季的小青菜金贵,天热难种,且虫多,不打药,大部分会喂了虫子,产量颇低。每天傍晚浇水的活,我们小时候总是逃不掉。

当然,要是夏至能用小青菜裹馄饨,七月半能用小青菜做馅摊茄饼,无论是拌肉馅,还是豆腐或青豆子,对于我小时候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珍贵的。直到1980年代分田到户后,我才在夏至和七月半,能放开吃上小青菜肉馅的馄饨和茄饼。
但是,故乡另一种青菜,秋种冬吃,不仅容易种,产量也大,而且不用打药——按我母亲的说法,虫子都给冻死了;更为要紧的是,这种青菜,不像夏天的小青菜,瘦骨伶仃没肉样,而是头大帮厚叶肥,味道非常好,尤其经霜之后,更是糯软清甜可口,其余蔬菜不仅味道难以匹敌,产量也是。
这种青菜,在我故乡叫大头青,以其菜头大著称得名(另有一种颜色较深,个头小一些,塌趴着的,叫乌塌菜,是大头青的一种)。上海人喜欢叫这种菜上海青,苏州人喜欢叫苏州青,但常州无锡人从未以地名冠之,而是统统叫做大头青。
我的家乡瓮安在贵州黔南,她是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在我的家乡春节也叫做“过年”,这是我们小朋友一年中最高兴、最难忘的时候。每当春节时,街道两旁的路灯杆上挂着火红火红的灯笼。
在整个江南地区农村普遍栽种的时候,以地名名之,格局太小。我小时候只知道大头青,后来见识渐长,依旧顽固地坚持大头青这个菜最质朴的乡野名字。
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自留地上,房前屋后的空地上,都会种大头青。整个冬天,大头青和白萝卜,是我小时候故乡乡村过冬过年的唯二当家菜。
在我还是个顽劣乡村少年时,无论是在江南肥沃的地里讨生活,还是洗脚进了学校读书考试;无论是不到8岁就流连灶台炒青菜,还是随着大人走亲戚吃喜酒,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青菜有多好吃,甚至,常常厌烦。毕竟,秋冬季节中午,无论在家还是上学,青菜都是当家菜。只有过年和请客时例外。
我后来回忆,少年时不是很喜欢吃炒青菜,除了吃多了生厌之外,导致吃厌的重要原因,就是那时炒青菜放油太少。那个年代,乡下的菜油太金贵了。
我小时候炒青菜,祖母下地干活之前洗切好一大篮青菜,只留破调羹半勺都不到样子的菜油给我炒青菜用,限量,这样的青菜味道,对于正在快速长身体的我来说,贵州作文400字,自然难以忍受。
今年我去贵阳过年,就讲一讲贵阳的春节习俗.年夜饭,是最隆重的一餐,是一家人的团圆饭.全家老小欢聚一桌,先要向老人祝福敬酒,敬菜,然后,大家相互敬酒,祝福平安.守岁,满室灯火通明,炉火旺盛,表示全家兴旺.全家人围炉团座。
但我从未对青菜荤烧生厌过,烧鱼,或者和肉圆或肥肉烧——我至今记得难得秋收后生产队集体聚餐时用青菜帮和肥肉片一起炖煮的菜汤的美味,尽管如今谁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菜帮子白肉汤了。
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目前集观光、度假和深度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新型和谐旅游目的地正在悄然形成。正如世界旅游组织所称赞的贵州是“生态之州、文化之州、歌舞之州、美酒之州”。
我对炒青菜生厌的感觉,待我到北京上学,就戛然而止了,青菜点点滴滴的美好,开始复苏。
1989年早春,我大四,寒假开学,弟弟还未开工,跟我到北京游玩。我故乡小村,读书出来在京工作的有数家,我带弟弟去拜访在京的同宗长辈。长辈留饭,其中一道菜叫香菇油菜。
弟弟听说菜名后,吃了一惊,悄悄问我:怎么油菜还能吃?弟弟有此疑问,是因为故乡的油菜,只指收菜籽榨油的油菜,间苗时拔下的油菜,猪羊都不吃,更别说人了。我告诉弟弟,就是香菇炒青菜。
吃完饭告别长辈后,弟弟忍不住问我:怎么北京的青菜炒不烂像生的一样?
弟弟的疑问,即是我对故乡的冬日大头青重生爱意的缘起——我到北京上学后,才知道北京的油菜(青菜),不仅炒不烂,还柴,味同嚼蜡,几乎无从下咽。少年时曾被厌弃的江南大头青,顿时在味蕾和脑海里鲜活翻滚起来。
江南的大头青,别看长得戆头厚叶,但菜也不能貌相,这粗犷的外表下,大头青其实柔嫩多汁,只需油盐翻炒,稍许即熟,无需其他佐料,出锅满室清香,味道清甜糯软。
一眨眼,到了春节末期,春节在正月十七结束了。大人们开始勤劳的工作了,而学生却还可以休息十几天。一年的新气象又开始了!是啊!这就是丰富多彩的贵州春节。一家人其乐融融。既热闹又喜庆!
尤其霜雪之后,更是清甜,以致许多北方人包括我家夫人,刚一接触,都吃惊以为加了糖。但这菜不放糖,是自然恩赐的甜美。以我如今之见识,蔬菜中能有如此甜美味的,我未曾遇见过。

它的名字叫“年”,它经常吞食过路的人们,可把人们害苦了。后来,出现了一位白胡子的老公公,他制服了“年”。人们为了防止“年”再跑下来,就用放鞭炮、贴红纸来吓“年”,所以就有了现在过年的习惯。
我的妈妈是贵州人,从小,我就没的去外婆家。小时侯,看着别的小朋友去外婆家,我心里很羡慕,常常缠着妈妈要外婆,妈妈总是说:“以后带你去看她。”可这个以后从没到来过,慢慢地我也就不提了。去年寒假。
我离开家乡后即爱上了大头青。每年冬天回家,再也没有厌过清炒大头青。一来有了北京油菜的比较,二来更是改革分田到户后农村生活的改善,油和荤物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稀罕宝贝了,家家吃得起油和肉了。有了油,上天恩赐给青菜的味道自然就不再有约束,完全释放了。
1994年春节前夕,我带新婚的夫人回故乡过年。此时已是小年夜的傍晚,下着雨,甫出常州火车站,空气中弥漫的都是我熟悉的大头青的味道,这才是我熟悉的故乡的味道啊。但自小在北京生活的夫人当时却很不习惯,甚至觉得有些恶心,她要经过几年后才习惯并爱上江南大头青的味道。
当然,大头青除了清炒,还有许多做法,可以加肉圆炒,猪油渣炒,下火锅,也可以做馅——至今我最爱的馄饨就是青菜猪肉馅的,还可以切碎烧鱼!
切碎青菜烧鱼是我家冬日别出心裁的一道创意菜。我父亲是附近乡村著名的捉鱼佬,家里鱼多,但旧说砍柴富捉鱼穷,其时能买得起的人少,自己吃又费油盐,所以冬日家里烧鱼时常常放上一大锅青菜,目的无非是不浪费油盐,青菜多了可以多吃几顿,尤其是吃鱼冻。后来条件好了,家里再也没有这样做过。母亲说,过去是因为穷才这样做,现在谁愿意这样搅在一起啊。

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就是笑不起来,我只是在哪里看一本书名字叫《莫言》我很认真的看着,在看着那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还有班主任,然后继续埋头看我的书。三年的我们共同走过,留下的是无尽的回忆。记得军训的时候。
但是,我后来在北京生活,发现如今养殖的鱼和大棚栽种的青菜,各自烧缺点明显,味道不好,按母亲她们老法合在一起烧,却是别有天地,青菜和鱼汤及鱼冻尤为鲜美,这是相遇之美。

不过,早些年,在常州,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冬日的味道,就是清炒大头青的味道,而非那些名贵的江河湖鲜味。这是当年江南日常饮食的底色。如今因为生活改善,城乡冬日餐桌虽然依然少不了,但曾经弥漫空中的味道,已经湮没消散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特殊味道中了。
在北京生活很多年后,社会的开放,物流业的进步,北方的江南菜也多了起来。
有一年我下班回家,岳母做了一盘青菜炒鸡蛋。我尝了一口,跟太太感慨岳母手艺,竟然能做出江南大头青的味道了。太太回:你嘴真够刁的,这是妈特意为你在菜市场买的南方青菜!我哈哈一笑,说,这菜还没经过霜打,味道还差点,经霜之后,就更好吃了。
虽然,如今货畅其流,不仅在北京的沪苏锡常风味的饭店能吃到,菜市场也有供应。我并非好龙的叶公,冬日或早春在故乡风味的宾馆如北京的常州宾馆必点清炒大头青,我也常跑菜市场买模样相似的青菜。但是,那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故乡青菜味道,都是形似味近而神不是。
无他,如今大都市的蔬菜供应,多是大棚规模化生产,甚至更像是工业化生产,产量更大了。甚至太阳、雨水和土壤等自然之物不再是决定蔬菜质量的因素,代之以的是人力,是现代科技,过去期待的应时而食正在为四季常有的丰繁所取代。

这样栽种出来的菜,与人和自然的关系远了,不再像过去那么亲近和让人有期待,外形和味道当然也不太一样了。大头青也是一样。而原来的蔬菜,贵州家乡的风俗作文,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也更像农耕时代的口味。
甚至,即使连弟弟靡费邮资从故乡快递至京的自家依着传统法子栽种的青菜,味道总也是差强我意,只能解馋一慰乡思。
无他,毕竟隔着千山万水,物流再神速,怎敌我故乡霜雪后想吃就地就割下锅之鲜嫩!

我写过不少与美食相关的文章,朋友送我顶“美食家”的帽子,其实我是不敢冒领的。
我真正喜欢的,更多本质上是能够填饱肚子的家常口味的食物,原材料随手可得,或者价格低廉,归根到底大众化平民化,一点不像美食家那般精致讲究,我也没有能力资格对食材烹调手法有过多讲究。大头青于我,就是此理,更何况它曾伴我成长。

我们家至今每年仍种许多青菜。2020年上半年,我因疫困守江南,几乎每天都有两顿素炒青菜,但我从未像小时候那样厌烦过,而是甘之如饴。
我更发现了即使冬日冷青菜汤拌饭,也是极其鲜美独特的吃法。回家过了饭点,我就是这样用剩大头青及菜汤拌饭。

侗族:芦笙会。贵州、湖南一带的侗族同胞,春节期间盛行一种“打侗年”(又叫芦笙会)的群众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只不过比“团拜”显得更加欢乐、热烈。两队在广场上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伴随着乐曲,翩翩起舞。
这都是从地里即割即炒的啊。而且那是父母兄弟种的,也是我和故乡的联系。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此福气?
我很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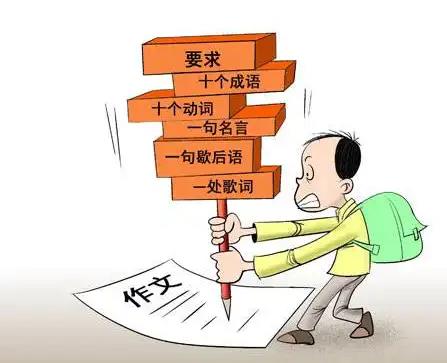
等女儿考上大学,我也到了回家频翻种菜书的时候了。
我爱故乡冬日的大头青。